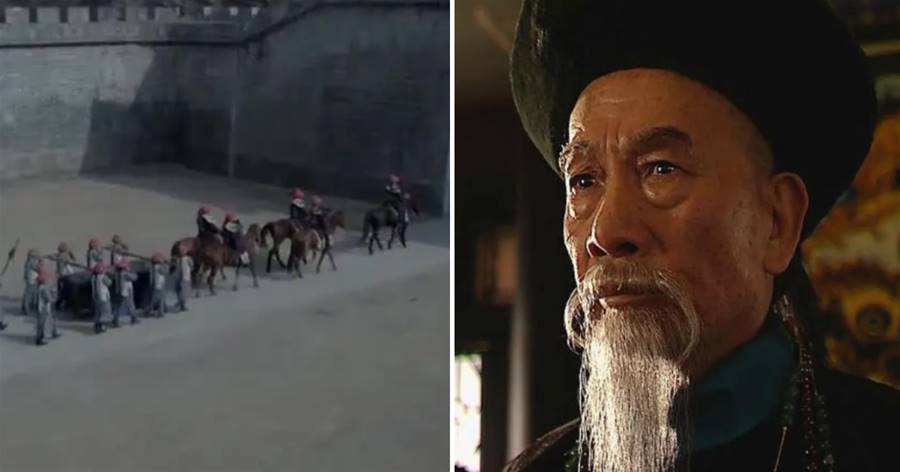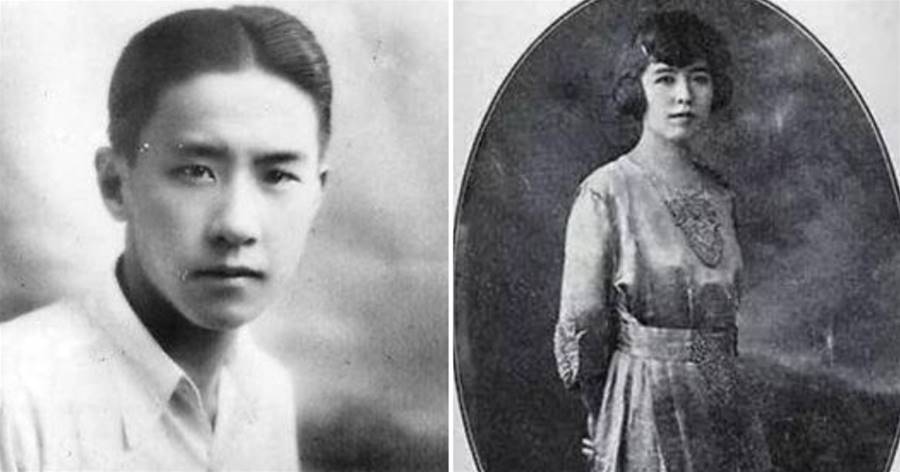今天,我們來聊一個真正的未解之謎——哈馬爾-達班山難事件。

事件發生在1993年的8月,地點是俄羅斯貝加爾湖南邊的哈馬爾-達班(Khamar-Daban)山脈。
這片山脈最高峰海拔2396米,8月平均氣溫11.2(±0.5)℃,罕見降雪。
也就是說,這是一起發生在夏天、低海拔并且沒有冰雪環境的山難。
這是一段當年搜救隊拍攝的畫面,他們找到了6名遇難者,有3人身上只穿著單薄的內衣,有兩人光著腳,像是要躲避什麼東西一樣。
這起山難有一個幸存者,但她在獲救以后再也沒有露面,故事整整沉默了26年。

直到2019年,這位幸存者突然出現在了電視節目上,她講出了當年的可怕細節……
時間回到1993年,8月1日,一群來自哈沙克斯坦的年輕人抵達貝加爾湖南岸。

這是一個圍繞著火車站建立的小集鎮,叫做穆里諾(Murino),小鎮緊挨著貝加爾湖,往南就是哈馬爾-達班山脈。
這片山脈風景優美,每年5-10月之間并沒有冰雪覆蓋,即將出發的這群年輕人也不過是一群校園徒步團的學生們,最小的15歲,最大的也才24歲。
三男三女,加上帶隊的女老師,一共7人。
老師叫做科洛維納(Lyudmila Korovina),這年41歲,是個徒步專家,獲得過蘇聯頒發的體育大師稱號(Мастер спорта СССР)。

她有點兒像我們新東方名師的感覺,家長們都很信任這位老師,暑假期間,把小孩交給她,讓她教授孩子們野外課程。
一年前,科老師剛剛帶著大家完成了天山山脈的徒步穿行,難度等級四。
這次他們又來到哈馬爾-達班山脈,科老師選擇了一條難度等級三的路線,線路全長約有230公里,繞行半個哈馬爾-達班,難度并不高,更像是一場夏季觀光,并且,科老師6個月前就開始準備這條線路,她對山里的情況非常熟悉。

就這樣,8月2日,小隊出發,與此同時,科老師16歲的女兒,也帶著另一支小隊出發了,這支小隊選擇的是一條難度等級四的線路,要橫穿哈馬爾-達班的腹地,科老師和女兒約定,兩隊在山里的帕托湖(Patovoye Ozero)會和,然后共同完成后面的旅程,前往目的地斯柳江卡(Slyudyanka)。

進山前,科老師按習慣,查看了天氣預報——未來7天,一切正常。
剛剛進山沒多久,大家就發現,天氣預報錯了……

淅淅瀝瀝的雨水落了下來。
隊員們不得不拿出雨披,在雨中繼續前進。
問題不大,當時他們每人的背包里都還有一套精心準備的干毛衣,被裝在防雨袋當中,如果持續大雨導致氣溫驟降,干毛衣可以拿出來保暖。
就這樣,小隊在雨中走了兩天,8月4日,他們穿過了朗古台山口(Langutayskiye Vorota),開始攀登汗烏拉山(Khanula),這是哈馬爾-達班的第二高峰——海拔2371米,小隊要沿著山脊翻過去。
中午以前,小隊攀登到了海拔2000米以上,到了這個高度,森林就消失了,山脊上是一大片高山草原。

本來,這里的景色非常優美,但現在,山上的雨越來越大,還出現了雷暴天氣,重重的雨點砸在隊員們身上,他們稍微停留以后就不得不立刻出發,他計劃在雷暴中快速通過山脊,但泥濘和大風還是延緩了他們的計劃。
下午4點,小隊移動到了海拔2310的位置,這幾乎就是汗烏拉山(2371)的頂點了,只要再堅持一下,翻過去,下山就能重新進入森林。

森林里的樹木不僅可以避雨,最重要的是可以擋風,現在氣溫雖然還有10℃,但山頂的大風和潮濕的衣服都正在持續奪走身體的熱量,隊員們的體感溫度要比10℃低很多。
從2310的位置又走了6公里以后,天色黑了下來,這個時候,科老師決定讓大家就地扎營,他們要在山上過夜。
于是,隊員們扎了兩頂賬篷,男女各一頂,分別蜷縮進去,還好是夏天,氣溫并不算太低,熬過今晚,明天就可以下山了。

但到了凌晨四點,狂風撕裂了賬篷,雨水灌了進來,直到早上六點,風停了,每個人的睡袋都是濕的,有隊員開始嘔吐。
簡單地吃過早飯以后,重新打包裝備,8月5日,上午10點,隊伍開始下山,這個時候有雪花落了下來,男生們開始抱怨,說他們又濕又冷,還找不到任何地標。
三個男生分別是,23歲的亞歷山大(Krysin Alexander Gennadievich),莫斯科國立科技大學的學生,從12歲起就參加徒步團,是小隊里最強壯的一個隊員,另外,他從小就是科老師看著長大的孩子,不久前還剛剛向科老師的女兒求過婚,科老師也直言不諱的把這個準女婿叫做——兒子。
19歲的丹尼斯(Shvachkin Denis Viktorovich),最開始他并不在小隊名單當中,是因為有一個孩子的父母不讓參加,丹尼斯才頂替那個人加入了進來,他加入時,父母正在度假,他并沒有得到父母的許可,只是自己留了張紙條說,我去爬山了,很快就回來。

15歲的帖木兒(Bapanov Timur Balgabaevich)他在一個登山世家長大,是徒步團的積極分子。
三個女生分別是,24歲的塔婭娜(Filipenko Tatyana Yurievna),剛剛畢業,在一所師范大學擔任領導秘書,非常喜歡爬山。
16歲的維多利亞(Zalesova Victoria)她本來是被科老師拒絕的小隊成員,因為在去年天山徒步的時候,她因為太疲憊而崩潰、發脾氣,科老師很不喜歡這樣的隊員,但這次,維多利亞非常喜歡哈馬爾-達班,她是求自己媽媽給科老師打電話,又保證不會再發脾氣,才被允許加入小隊。
最后一個是17歲的瓦倫媞娜(Utochenko Valentina),哈薩克斯坦彼得羅巴甫洛夫師范大學的學生,正在學習旅游體育專業,未來也可能成為和科老師一樣的徒步團教師。
這支小隊當中,沒有人是菜鳥,雖然被大雨淋了3天,但現在只要按計劃下山就沒有太大問題,然而誰也沒有想到,就是男生們的抱怨聲中,死神突然就來了。
最強壯的亞歷山大突然跌到,被扶起來以后依舊是走得跌跌撞撞,科老師覺得不對勁,于是決定一個人留下來照顧這個準女婿,讓其他隊員先往前走。

但走了沒多遠,大伙兒又都紛紛跑了回來,因為,他們聽見科老師在求救,原來,亞歷山大這會兒已經開始口吐白沫,身體抽搐,科老師需要大伙兒的幫助,接著,塔婭娜支起一個遮陽棚,其他人在旁邊幫忙。
瓦倫緹娜和科老師一起照顧亞歷山大,但眼看著亞歷山大就開始流鼻血,同時,他驚恐地睜大眼睛,眼睛也開始往外滲血,瞳孔正在放大,臉色也瞬間變得慘白,瓦倫緹娜感到亞歷山大的體溫正在消失,而這個時候科老師也說,他沒有脈搏了。

誰也沒想到死亡來得這麼突然,短短幾分鐘而已,所有人驚魂未定,但突然又發現,一向嬌氣的維多利亞也已經倒在了草地上。
科老師她讓瓦倫緹娜去把她扶到遮陽棚這邊來。
但是,當瓦倫緹娜去扶維多利亞的時候,瘋狂的維多利亞則開始兇狠地撕咬瓦倫緹娜的手臂,瓦倫緹娜想找人幫忙,但回頭看的時候卻發現,科老師那邊,塔婭娜正在用腦袋撞擊巖石,男孩兒丹尼斯躲到了石頭后面,正在往睡袋里鉆。
似乎大家都被什麼東西嚇到了一樣,瓦倫緹娜扔下維多利亞,趕緊跑過去查看,原來,科老師也和亞歷山大一樣,正在口吐白沫,七竅流血。
瓦倫緹娜又推了推旁邊的帖木兒,他也已經不動了。
這個時候,被嚇傻的瓦倫緹娜突然被丹尼斯踹了一腳,丹尼斯說,趕緊下去,風很大,瓦倫緹娜幾乎是抓著自己的背包連滾帶爬的被大風吹下了山,丹尼斯一開始似乎還跟在后面,但最終,瓦倫緹娜并沒有看到丹尼斯下來。

進入森林以后,瓦倫緹娜害怕極了,剛剛似乎是一瞬間,所有的同伴都倒下了,而自己什麼時候發作呢?
瓦倫緹娜穿好備用的衣服,用遮陽棚蓋住自己,躲在睡袋里,就這樣驚恐地渡過了8月5日這天。
第二天一早,瓦倫緹娜上山查看,所有人都保持著昨天的位置,沒有人還活著,口吐白沫,當時瓦倫緹娜認為大家都死于肺水腫。
但她不敢多想,從隊員那里收集了指南針和地圖以后,就再次獨自下山,尋求救援。

然后,她獨自在山里走了四天四夜,雖然已經沿著地圖下到了斯涅河(Snezhnaya),但她依舊沒有找到居民點,這個時候,她也已經開始發高燒,肺部還出現了水腫的跡象,不停的干咳,呼吸困難,意識也正在逐漸模糊,她後來在電視節目里說,自己當時不想這麼臟兮兮的死掉,于是,就強忍著高燒,爬進了冰冷的河水里面,打算把自己從頭到腳都洗干凈以后再迎接死亡,但就在這個時候,她突然看到河道拐彎處來了一艘明亮的雙體皮劃艇,瓦倫緹娜尖叫著揮舞雙手,原來這是一隊來自烏克蘭基輔的游客,他們救了瓦倫緹娜。

與此同時,8月5日,科老師女兒的隊伍順利抵達帕托湖,這是兩隊約定的會和地點,女兒在這里整整等了兩天,也不見科老師他們從森林里出來,于是,女兒帶隊離開,8月18日,女兒順利抵達目的地——斯柳江卡,她立刻向救援人員報案,但因為天氣原因,救援直升機直到21日才起飛,救援隊24日才到達事發地點。
這個時候離8月5日山難,其實已經過去了20天。

不久以后,法醫得出結論,除科老師死于心臟驟停以外,其余5人全部死于失溫癥,也就是俗稱的被凍死了。

另外,法醫還發現,遇難者都有營養不良的現象,肝臟和肌肉缺乏糖元,多器官缺乏營養,這大概相當于我們俗稱的被餓死、累死了。
這樣看來,法醫的結論是,除科老師死于心臟病以外,其他隊員們都死于饑寒交迫,為什麼會這樣?
當時,大概有這樣幾種理論來解釋。
事發后,當地搜救局的副局長,尤里(Yuri Evgenievich Golius )接受了采訪,他說,自己很早以前就認識科老師。

科老師非常嚴格,有一次自己在貝加爾湖北邊和科老師相遇,當時科老師帶著兩個十六七歲的男孩兒從山上走下來,那兩個男孩兒看起來非常疲憊,其中一個連開路用的柴刀都舉不起來。
自己把男孩兒們接到營賬里面來,剛一拿出茶葉和面包,男孩兒們就撲了上去,他們就像好幾天沒有吃過東西一樣。
當時,尤里記得科老師還跟自己說,今后打算開一所生存學校,帶很少的食物和衣服進山,然后磨礪意志,培養孩子們的品格。
尤里說,自己當時心里很生氣,那兩個孩子還是青少年啊,科老師不應該用自己專業運動員的要求來折磨小孩子。
結果,在這次搜救現場,尤里又看到了類似的情況,他仔細地搜查了營地,只找到一罐空肉罐頭。

尤里說,試想一下,山頂上下著雨夾雪,冷得要死,科老師卻命令大家把一罐燉肉分成七份,尤里在搜救的過程中還在祈禱,也許自己能在營地里找到糖果或者巧克力的包裝紙,但什麼都沒有。
隊員們在嚴寒中就吃了那麼一點點東西,難怪他們會營養不良。
尤里的說辭似乎完美地解釋了官方給出的死因——失溫癥和營養不良。
但仔細想想,現場搜救隊只發現了一個空罐頭,這也并不意味著隊員們早餐只吃了一盒罐頭,搜救隊到達,已經是20天以后,所以,完全有可能其他食物的垃圾早就被野獸叼走,或者被大風吹到了別的地方。
當時,媒體們打算像幸存者求證小隊的飲食情況,但瓦倫緹娜卻像人間蒸發一樣,沒有人知道她獲救后去了哪里……
搜救隊發現6名遇難者的時候,有3人撕破了自己的外衣,只穿著單薄的內衣,有兩人光著腳,看起來像要逃避什麼東西一樣。
這個現象在大眾和媒體們看來非常詭異,于是,紛紛提出質疑,這個時候,登山專門家出來說話了,他們說,這種現象看似異常,但卻恰好符合失溫癥的表現,叫做反常脫衣現象,這是因為體溫在低于32℃以后,下丘腦中調節體溫的中樞會產生錯亂,釋放了身體很熱的信號。
隊員們會在這種錯誤信號的指引下開始脫衣服,還會不受控地發狂,所以才出現了眼前的現象。
這種反常脫衣的現象,在其他山難事件中也有發現。
專家的話看似有理有據,但這次不一樣啊,當時就有一個救援隊的成員(Valery Tatarnikov)質疑過專家的說法。

他說,已知的反常脫衣現象都發生在冬天,而且這種現象并不常見,至今還沒有發現,5人死于失溫癥,5人都出現反常脫衣現象的案例。
更何況,小隊遇難是發生在夏天,像他們這樣的專業隊伍,不可能被凍死,即使淋了幾天雨,衣服全部濕透了,山頂的強風又在持續奪走體溫,這種情況下,團隊只需要20分鐘生火,那樣無論如何他們都獲救了。
但他們為什麼不生火?另外,他們為什麼選擇在山上過夜?即使太累了,不得不在山上過夜,那離他們30分鐘路程的地方,就有一個避風港營地,他們的地圖上有標注,但他們為什麼不去哪里?
還有,每個人背包里都有干毛衣,為什麼干毛衣都沒有被使用過的痕跡?
很顯然,這意味著,當時他們并沒有感到很冷,團隊也并不認為在山上過夜就一定會被凍死。
而且,事實情況不也是這樣的嗎?
搜救隊在現場發現了早餐的痕跡,團隊是在第二天吃過早飯以后才紛紛遇難,這顯然和失溫癥理論不相符。
會不會是因為第二天早餐的有問題呢?

幸存者瓦倫緹娜提到,隊伍一路上都在按照科老師的要求,采集一種叫做金根(золотой корень)的植物。

這其實就是中文當中的紅景天,這是一種生長在高海拔地區的珍稀植物。
而且救援隊也在遇難者的背包中發現了大量的紅景天。
按照瓦倫緹娜的說法,自己一路上也是靠生吃金根才能以幸存,而且,隊伍在山上耽擱了,其實也是因為大家在忙著采集金根。
那會不會在采集的時候,不小心混入了一些毒蘑菇呢?

第二天早餐,煮金根的時候,這些毒蘑菇又不小心被一起煮了,然后導致集體中毒。
蘑菇中毒以后,確實會出現吐口白沫、七竅流血的癥狀,同時還會出現幻覺和發狂的癥狀,這也符合幸存者描述的用頭撞巖石,發狂咬人的現象。
所以,這是食物中毒嗎?
很顯然這個理論也經不起推敲,首先,科老師本身就是一個草藥大師,她不太可能讓小隊誤食毒蘑菇,另外,幸存者瓦倫緹娜也吃了同一鍋早餐,她為什麼沒有中毒?
這個理論是搜救隊的尤里提出的,首先,他認為,科老師他們背包里出現了大量的金根,不排除是為了下山以后販賣。
而這個行為,很顯然已經冒犯到了當地人的信仰。
因為,當地的居民是一群叫做布里亞特(Buryates)的蒙古人,他們信仰藏傳佛教和薩滿宗教,其實和我們內蒙、西藏的蒙古族類似,他們也認為,紅景天是一種神圣的植物,人類不應該貪得無厭的去獲取。

而且,哈馬爾-達班在當地蒙古人的語言當中,本來就是可怕石頭的意思。
最開始,哈馬爾-達班,專指貝加爾湖岸邊的一小段山脊,這段小山脊在遠古的匈奴時代,就是一座獻祭的祭壇。

祭壇切開了兩片沿海的平原,直挺挺的[插·入]到貝加爾湖當中。
所以,整個哈馬爾-達班在當地從來就不是什麼風景優美的旅游勝地,而且團隊遇難的那座汗烏拉峰(Khanula)其實就更是一座不吉利的妖山。
傳說,很久很久以前,有一位古代汗王被逼上絕路,在這座山峰上面,汗王自盡了,他采用了草原人最恐懼的自盡方式——一點點放干自己的血液。
草原人認為,人的靈魂在血液當中,所以,這也就意味著,汗王拒絕轉世,他要讓自己的幽靈永遠寄生在這座山峰之上。

當地人對這座山峰充滿了敬畏,是無論如何都不敢隨意采摘那上面的紅景天的。
但科老師他們卻采了,還因為采集太多而耽擱了下山的時間。
幸存者說,在山上大雨突然變成了雷暴,很顯然,這在蒙古人的信仰當中,會被認為是一種來自薩滿的詛咒。
小隊會不會真的是遭遇了某種大自然的神秘力量呢?
果然,也有人提出過類似的理論。
有一個搜救隊成員(Nikolai Fedorov)認為,當時小隊扎營的山脊,從地形看就有問題,這里恰好處在一個不寬不窄的峽谷當中,整晚的強風有可能在山谷間產生次聲波。

這些次聲波雖然聽不見,但對人體有傷害,與此同時,當晚的雷暴也可能在山谷里電離出大量的臭氧,這些臭氧在清晨濃度很高,臭氧中毒也會出現神經錯亂的情況,團隊有可能是遭遇了次聲波和臭氧中毒。
這個說法雖然新穎,但很難被客觀還原,另外,也解釋不了為什麼幸存者瓦倫緹娜不受影響。
這是很多愛好者都熱衷的一個都市傳說,因為,根據瓦倫緹娜的描述,口吐白沫,身體抽搐,眼睛、鼻子流血,這很像是一種前蘇聯神經毒劑的中毒現象,包括科老師心臟驟停的死因,這也符合這種神經毒劑的副作用。

這種神經毒劑叫做諾維喬克(Novichok),是蘇聯在1971年開發的,而恰好這種毒劑在1993年停產。
愛好者認為,有證據表明,毒劑停產前的最后幾次實驗,就是在哈馬爾-達班山脈中進行的。
所以,科老師團隊是因為不小心闖入了實驗場所嗎?
顯然,這里有一個解釋不通的地方,哈馬爾-達班并不是什麼無人區,尤其是8月,這是旅游旺季,軍方即使要試驗,也不可能選在這個時間和地點實驗。
同時,這個說法一樣無法解釋為什麼瓦倫緹娜不受影響。
但後來,愛好者們又發現了一個線索,那就是,這種毒劑可溶于水,它們在自然環境中,至少要4個月才能徹底降解。
這樣一來,軍方實驗的時間和地點就不需要與團隊重合,有可能是幾個月前在山上進行了實驗,然后暴雨把山上殘留的毒劑沖刷到了團隊扎營的地方,第二天太陽出來,毒劑揮發,就導致了小隊集體中毒的現象。
毒劑是從草地里揮發出來的,亞歷山大為什麼第一個中毒?
因為他摔了一跤,很可能在摔跤的過程中,接觸到了草地里的高濃度毒劑。
接著,俯下身去幫助亞歷山大的隊員們紛紛中毒。
而瓦倫緹娜為什麼沒有中毒,這很可能因為她被科老師支開,去幫助維多利亞,而維多利亞又兇狠的趕走了她,所以,在這個集體中毒過程中,似乎只有瓦倫緹娜在不斷移動,這可能導致她遠離地面,中毒不深。

同樣中毒不深的本來還有丹尼斯,但是,丹尼斯卻選擇躲到石頭后面,并且鉆入睡袋,這導致他也迅速中毒,在最后,他踢瓦倫緹娜下山的時候,已經中毒太深,無法再跟上來了。
這個猜測還有兩個側面證明,那就是,愛好者們認為,
1,瓦倫緹娜為什麼在獲救以后就消失了,她是否已經和安全部門簽訂了某些保密協議;
2,8月18日報案,為什麼21日直升機才起飛,24日搜救隊抵達事發地點?這延遲的7天,會不會是誰有意在等待毒劑消失?
這種說法顯然沒有任何客觀線索的支持,只能被當做一種都市傳說。
但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麼呢?
沒想到,等待了26年,當2019年幸存者瓦倫緹娜和科老師的女兒,這兩個當事人出現在電視上的時候,她們卻講了一段更奇怪的新故事。

2019年,當調查記者聽完瓦倫緹娜的故事以后,記者看著瓦倫緹娜起身,從衣柜里拿出了一串老舊的念珠。

瓦倫緹娜說,這是自己被救回斯柳江卡以后,一名當地救援人員給自己的,直到自己拿到這串連珠,才感到真的獲救了。
她相信這是某種人類與大自然的和解。
瓦倫緹娜還說,科老師絕對不是一個刻薄的人,當時他們每天的飲食都經過精確的計算,團隊里沒有人憎恨科老師,另外,在山上扎營前,他們嘗試過生起一堆篝火,但是失敗了,才不得不在寒風中過夜。
那晚真的很冷,賬篷破了,睡袋都濕透了。
接著,女兒又采訪中說,當時,在隊伍出發前,當地人就提醒過他們,今年山里很不正常,有一頭熊咆哮著捶打鐵路,還企圖擋住迎面撞過來的火車。
進山以后,女兒又總能看見有一頭巨大的麋鹿一直在沿途注視著他們。

女兒甚至還因為這頭麋鹿而繞路,耽擱了大半天的時間,從森林邊緣繞了過去。
果然,後來女兒的隊伍到達山谷的時候發現,山谷里是橫七豎八的樹木,這是剛剛發生過泥石流的場景啊,如果自己不繞路很可能遭遇這場泥石流。
後來女兒經常在夢中見到那頭麋鹿,她始終相信當初是麋鹿搭救了自己。
沒想到,當兩位當事人在26年以后首次發聲,卻講出了一個比神經毒劑更難以置信的自然傳說。
所以,到此為止,哈馬爾-達班事件依舊是一樁貨真價實的未解之謎。
它和1959年發生在烏拉爾山脈的佳特洛夫(Dyatlov Pass incident)事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,所以,也被稱作俄羅斯的第二起佳特洛夫事件。
但是,拋開那些西方人那些固有的理性分析和客觀調查,也有愛好者認為,這何嘗不是發生在大雪山區域內的第二起梅里雪山事件呢?

從云南的橫斷山到青藏高原再到蒙古和貝加爾湖,這里的原住民都信仰著藏傳佛教,他們都有著自己的神山信仰。
就像我們原來說過的一樣,梅里雪山故事里的幸存者——小林泰三,他從最開始發誓要征服神山,到最后被神山信仰所折服。

也許,瓦倫緹娜和科老師女兒講得故事并不奇怪,只是她們用西方人無比陌生的方式,講出了自己心中被種下的那個神山信仰。
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這里,謝謝大家。